作者:毕晔
“豁出去,活下来。”

提要
- 什么是“女性主义”电影,为何这类题材成了“香饽饽”?
- “失足”女性的真实状态是什么样的?
- 女性电影能激活“她力量 ”吗,应如何看待艺术作品与社会期待的关系?
- 彩蛋
编者按
从女性主义到女性主义电影
女性主义(Feminism),又称女权主义,是指争取女性权利、实现性别平等的人文主义思想与社会运动体系。这一思潮催生了女性主义理论。这套理论流派多元、议题广泛,围绕生育权、受教育权、薪资平等、反对性别暴力、批判父权制等展开讨论,强调提升性别意识、推动社会改革,目标是打破男性主导的权力结构与性别歧视,提升女性在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地位,建立一个对所有性别友善平等的社会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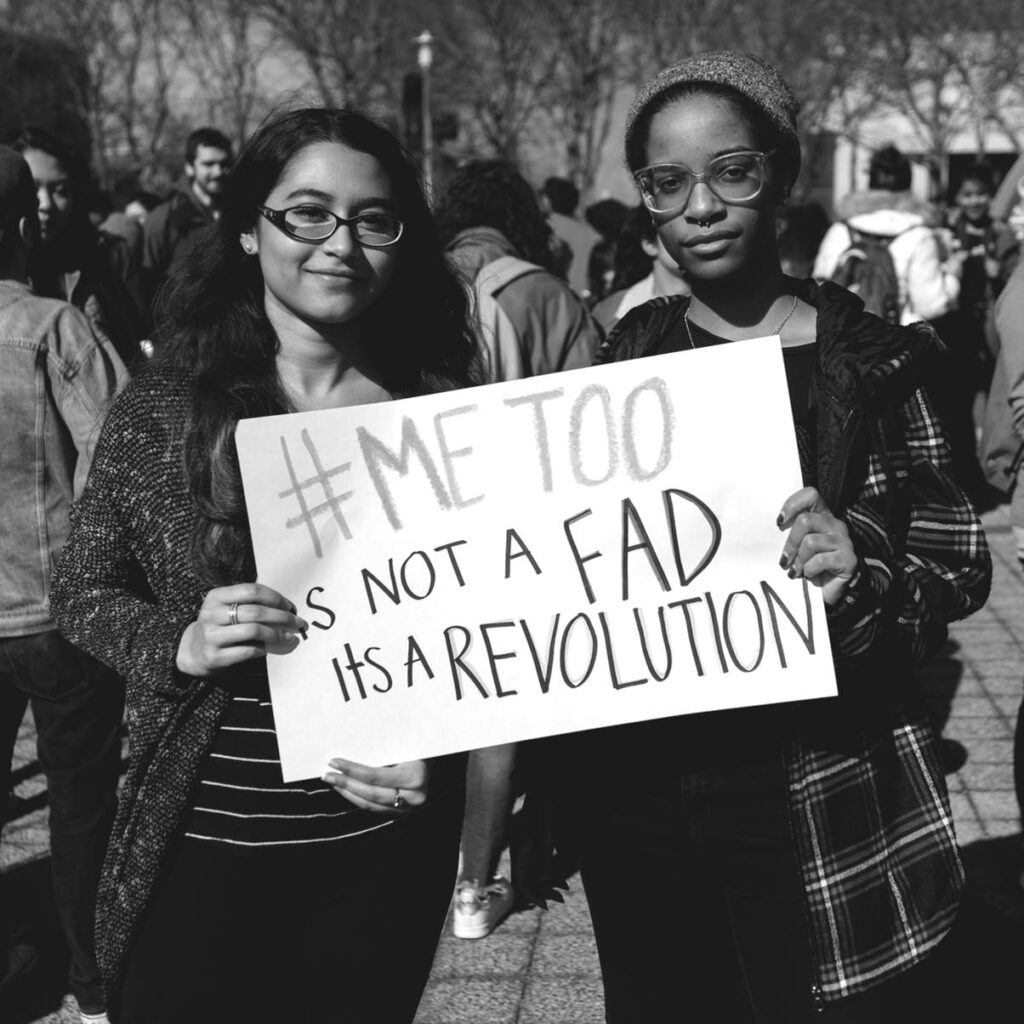
女性主义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:
- 第一波(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):源于工业革命和自由主义运动,主要争取女性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,尤其是选举权和受教育权,确认女性作为独立社会成员的身份。
- 第二波(20世纪60至80年代):受到嬉皮运动和共产主义思潮的影响,批判父权制,强调女性的经济独立、性自由、生育权利,推动法律与社会结构的深层次改革。
- 第三波(20世纪90年代):强调性别多元与交叉性,主张性别平等应同时关注男性权益,打破传统性别角色,促进不同身份群体之间的理解与协作。
- 第四波(2010年代至今):在MeToo运动、占领华尔街等社会运动背景下兴起,聚焦反性骚扰、经济与宗教平权,同时反思早期女性主义对非西方、少数族裔女性的忽视,形成更为多元、包容的理论与实践。
进入21世纪后,女性主义已成为跨越种族、宗教、文化与国家界限的全球性思潮,与人道主义和普世价值深度结合,持续推动世界范围内性别平等的进程。
女性电影理论在第二波浪潮中得到了发展,女权主义电影也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。1972年,第一届女权主义电影节在英国和美国举办,而第一本女性主义电影期刊:《女性与电影》也随之诞生。
可以说,电影艺术领域井喷式的创作,是女性力量崛起的一面“镜子”。
正文
1
中国的女性主义电影
以女性视角和女性叙事为重点的影视作品,近年来在中国也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势头。男导演、女导演、新导演、老导演都在往这个话题上凑,想在这里赚一波新的流量。
那么,什么是中国的“女性主义”电影呢?——是女性视角?是没有男性凝视?是讲述女性故事?还是说,它仅仅是替代“宏大叙事”的“清粥小菜”,给观众换换“口味”的“解腻”之作?其实,就像“女性主义”这个词条本身一样,“女性主义电影”也没有统一的定义。广义上讲,从《失恋三十三天》红起来的“小妞电影”(美国的chick’s film), 也算一种女性题材。

以我“浅薄”的理解,拥有大量女粉丝的男演员主演的电影,最多算“女性凝视”。所谓“女性主义”电影,必须还是得以讲述“女性”故事为主,且最好是女性来表达女性。为什么呢?单从生理结构、荷尔蒙分泌来说,男女差异太大了。世界上不乏 “暖男”,然而,男性无论多么“体贴入微”,都很难精准体会到女性在社会上打拼时面临的特殊压力和困难。举个简单的例子,再高明的男医生,都无法对“痛经”有切身体会。这不是水平问题、不是心态问题,而是生物属性决定了无法“感同身受”,“体谅”已经是一种善意了。
由此可见,女导演在女性题材上具有天然的优势,或者,主创团队里如果有女性话语主导者,可能会比较容易抓到观众的“脉搏”。不过,这里也有一些我回答不了的问题,比如,如果金星老师某天做导演拍了电影,算不算女性导演以女性视角拍摄女性题材呢?

说到中国电影行业的女性从业者,这里面也有些尴尬的场景。根据香港传来的片场“老规矩”,女性工作人员在现场时不可以坐金属器材箱——因为月经“不洁”,会带来“霉运”。 那么,问题来了:Lana Wachowski (原 Laurence Wachowski ,《黑客帝国》导演,现为“女性”)到了香港片场,能不能坐器材箱呢?当女性电影人不遗余力地将“大女主”形象托举于荧幕之上供人膜拜时,荧幕背后的她们在工作过程中是否也值得同样的尊敬(包括台前幕后的所有女性)?毕竟,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也已经过半了。
比“概念”更重要的是市场,所以,关键问题是:为何女性题材在中国越来越受到追捧,它吸引的是哪些观众?根据猫眼数据,2024年“爆款”女性电影《好东西》在票房贡献上,女性占81.5%,男性18.5%;一、二线城市占54.4%。另一部“大爽文”女性电影《出走的决心》,票房贡献上,女性占82%,男性占18%。由此可见,为女性电影买单的,绝大多数还是女性,且为都市女性。这一方面是因为,这类电影更多展现的是都市女性的话语权,迎合的观众本来就是这些人;另一方面,都市女性相对而言自主程度较高,追求也更为丰富,即,她们有这样的精神需要,消费需求又刺激了生产。在市场和资本的影响下,一个大火的题材,当然人人都想分一杯羹,乘着流量的风上青云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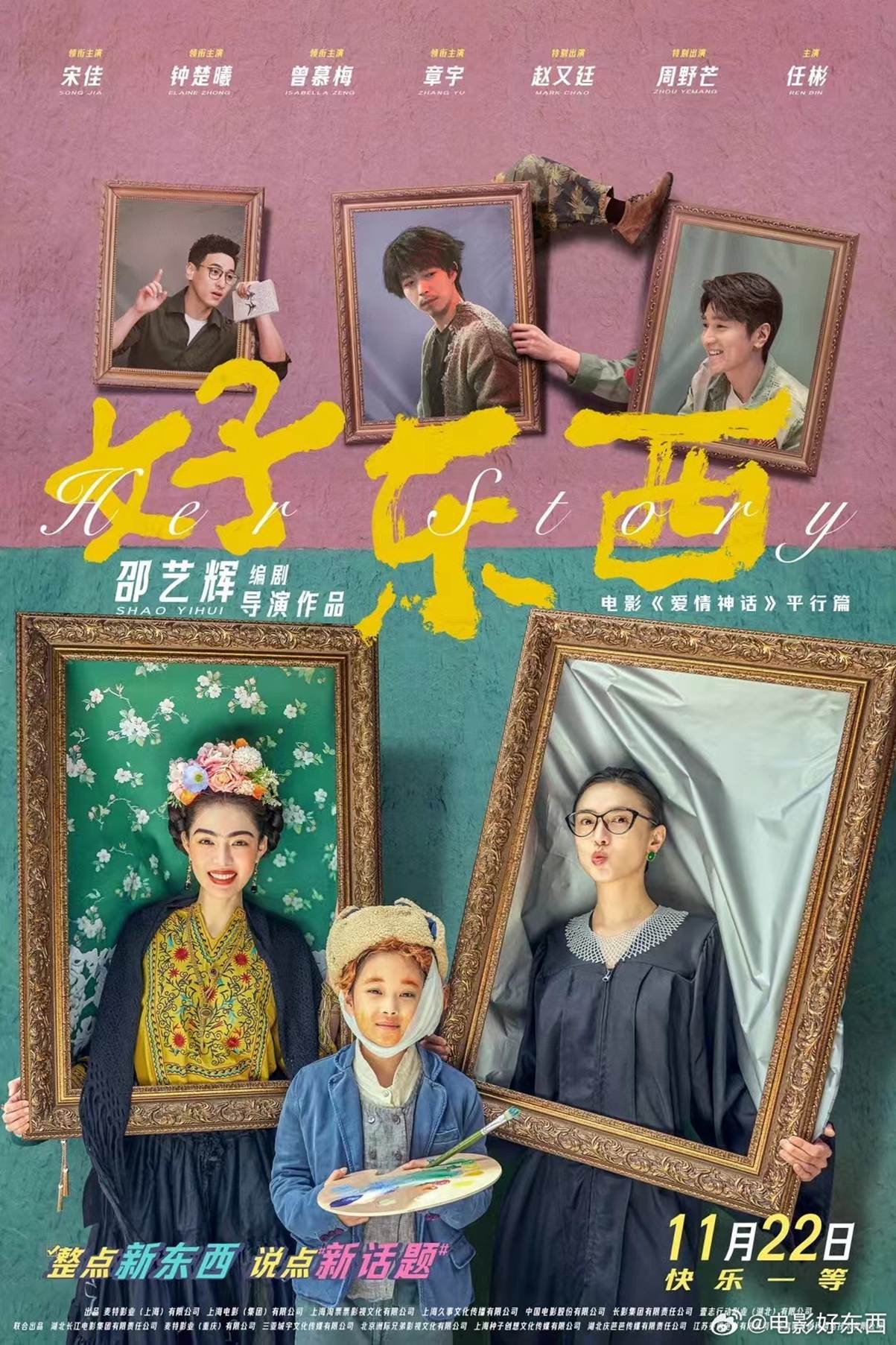
然而,有追求的电影人也不甘拾人牙慧,总希望能带出点“新风向”来。所以,即便同为女性题材,呈现上也在快速转变。这股“旋风”将把市场带到哪一个方向,大家拭目以待吧。
2
从女子监狱到《向阳·花》
先说一个大致的概念:大多数男性导演关于女性的叙事是“拉良家女下水,劝风尘女从良”——倒不是心思“猥琐”,而是,这是戏剧冲突最大的两件事。在一切高潮结局之前,有什么推动力能强得过“饮食男女”之间的普世矛盾呢?从关汉卿的《救风尘》到《Pretty woman》,古今中外不外乎如此。
因此,当我看到《向阳·花》剧本的时候,很难把这部电影和冯小刚联系起来。五代后男性导演镜头里,对女性有爱、有怜悯、有尊重。用“俯视”这个词有些过分,但骨子里多少还是带着一点点“男主外,女主内”的思想,更多把女性视为“半边天”,而不是浴血奋战的“战友”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情况下,即便是大女主的戏,多少也有点“变调”。当然,这并非“错误”,毕竟男女视角天然不同,勉强不来。
可贵的是,《向阳·花》里除了一贯嬉笑怒骂或普度众生的“冯式”笔触,也包含着一位男性导演从女性视角出发来说故事的诸多努力。电影里原有的感情线被砍的七七八八,为的就是弱化男性叙事,突出女性之间互助互爱的情谊。也许众口难调,效果无法让所有观众满意,但创作团队的诚意是实打实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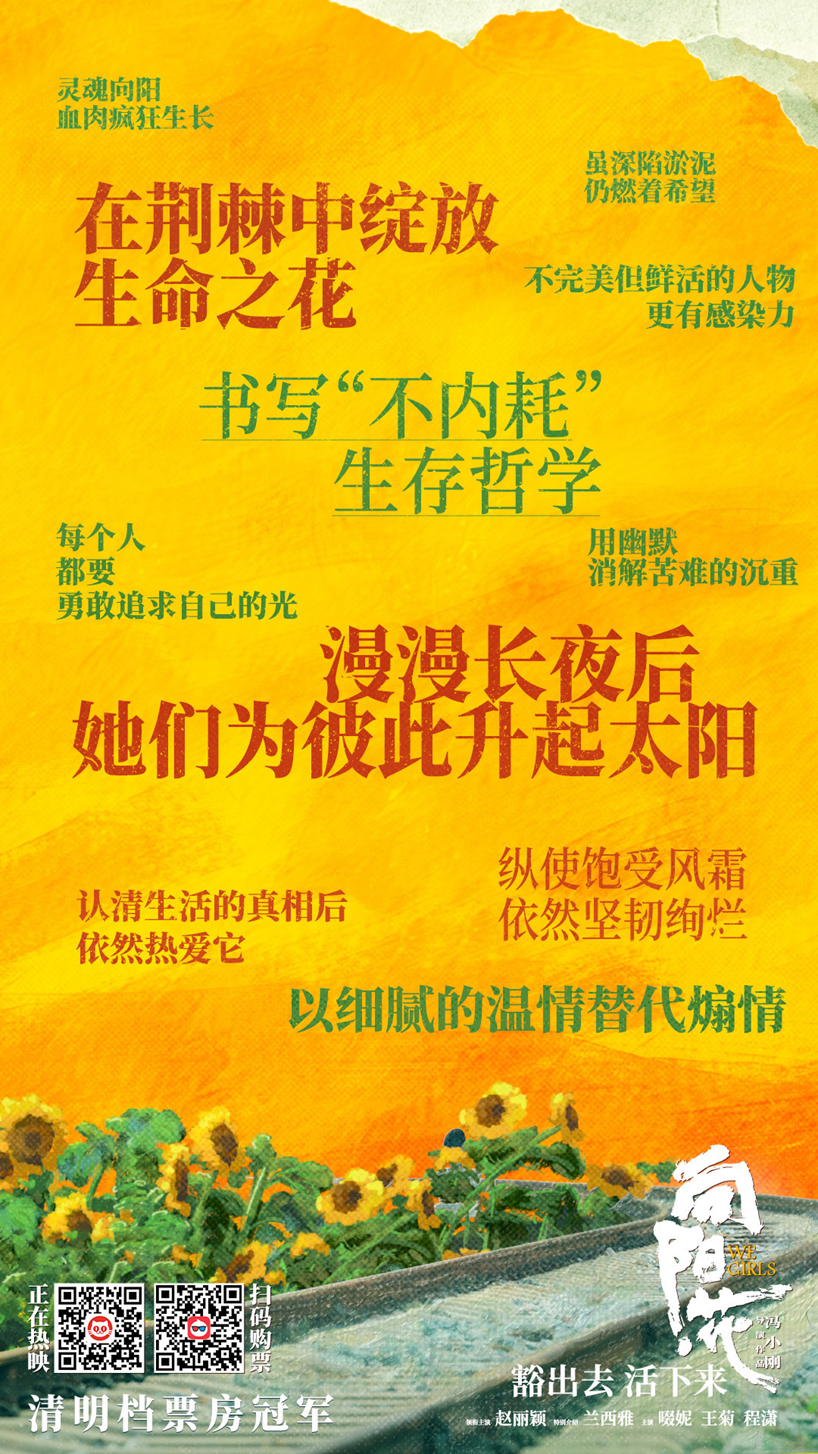
值得一提的是,《向阳·花》的主题与角色塑造与传统大女主电影差别比较大。影片讲述了几位女囚犯在刑满释放后,面对社会偏见和生活挑战,“不惹事也不怕事”,努力返回社会的故事。创作者们期望通过她们的经历,展现女性在困境中互助扶持、坚韧不拔、“豁出去、活下来”的精神。
这不仅是一部关于女性重生的励志电影,也是一部关注社会边缘群体、呼吁包容与理解的现实题材作品。在众多的女性角色中,“女囚”是一个很偏门的选角题材。为了更准确地抓住女性罪犯的特点,我们做了一些关于她们的资料研究。相对男性罪犯而言,女性更多涉及经济类犯罪、拐卖、盗窃、卖淫和诈骗。所有罪行中,“故意伤害”和“侵占财务”比重最大。而在“暴力犯罪”中,“故意伤害”的比例高于“谋杀”。
调研中我们还发现,婚姻不幸、家境贫困、失业、处于家庭弱势地位或长期性压抑的女性,犯罪比例相对较高。青春期的女孩在叛逆冲动和不良引导下犯罪的比例也有所增加。此外,对人际关系的不满和物欲的不满足也是女性犯罪的两大诱因。

探访女子监狱的经历更加意义非凡。它刷新了常人对女囚的刻板印象,让创作更贴近现实。举几个亲眼所见的例子:经济类罪犯大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女性,她们很“文气”。由于狱中不能有玻璃类的随身物品,她们的眼镜都换成了树脂眼镜。如果不是那一身囚衣,这些人的气质莫不是学校里教书育人的老师!而拐卖妇女儿童的女犯,也不是想象中一脸“尖酸刻薄”相。相反,她们看起来更像是没有记忆点的普通中年女性,却显得十分有“亲和力”,这可能是她们更容易混入人群的原因。
其实,大部分女囚都是心平气和,而不是满脸戾气的样子。根据这些信息,我们在选择“女囚”演员时,也不会倾向于“样貌惊人”的人。
当然,除了筹备电影,参观监狱本身对我来说也人生“奇遇”,产生了许多独特的感受。我常常说,我的工作一定会带我到世界上很多神奇的地方,监狱是最特别的之一了。当我跟着管教们挨个房间参观时,内心五味杂陈。其中最让我难受的是那些满头白发的女囚,我不禁为她们担忧:她们还能出去吗,这么大年纪出去后怎么办呢?当时还碰到教员们正在收监一位卖淫女犯。她约莫二十出头,懵懵懂懂,一脸无知与迷茫。那种毫无心机的破碎感让人觉得可惜又可叹。
这些人的人生将何去何从?出狱后是否能从断掉的地方接续?《向阳·花》里的姑娘们是幸运的。她们出狱后虽然饱受歧视,但可以抱团取暖,守望相助,陪伴彼此度过每一个寒夜。最主要的是,影片里的女子,无论社会待她们如何,她们没有自我放弃。而现实中曾经“失足”的女性,她们每个人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,是否还能拥有自强不息的精神?我们不得而知。
为了她们的未来,国家和监狱机构也是想尽办法。狱中特设“非遗”手工制品培训班,供女囚们学习手艺。这么做无非是希望她们出狱后能有一技之长,重新融入社会。
3
女性电影与“她力量”
我还想说一说观众对电影的“期待”问题。去年《好东西》引爆电影市场,口碑票房双丰收。但它在法国上映的时候,有影评表示“批判得不够深刻”,我认为“一针见血”。类似的反馈也出现于《向阳·花》,这也不意外。
然而,这里需要明确的是,电影作为娱乐载体,它只是人类艺术表达的一种形式。期望电影成为治疗社会问题的“灵丹妙药”就有点“不靠谱”了。郭德纲早期曾在他的相声里说:不能指望相声教书育人。电影也是一样的问题,它可以用艺术的方式揭露社会问题,但问题暴露之后,我们需要一整套社会机制来配合解决这些问题。
那么,对于女性主义电影,近几年的作品揭露问题了吗?——揭露了。深刻吗?——难说。比如《好东西》,因为是女导演的关系,天然缺少了男性凝视。它以一种嬉笑怒骂的方式在表达两性纠葛,但并没有告诉观众:我们在观察别人生活的时候,是否真的能为自己的将来寻找到新的方向?作为女性主义的支持者,我自然对这部作品有更多的期待,或者说“贪心”更多东西。可是作为电影人,也必须承认:电影表达问题,但不必解决问题。娱乐产品能让观众在观影的两个多小时里情绪价值拉满,它的本质任务就已经超额完成了。

另一个典型案例是《出走的决心》。故事说的是一个在婚姻中被冷暴力多年的苏阿姨,在孩子独立,自己退休后,用退休金独自开车环游中国,成为网红,最后离开冷漠的丈夫。原型苏阿姨的这股子狠劲,不失为结束不幸婚姻的一种方式。电影看得“爽”,但问题是,现实中又有多少人真的能够甩开一切独自旅行呢?我八十多岁的姨妈至今每年过年都要吃“烤麸(靠夫)”,这种深深打在骨子里的思想钢印,不会因为几部电影消失不见。同样的问题其实一直都在被反复提起,然而我们真有解决方案吗,或者说有苏阿姨那种毅然决然的勇气吗?
简单地用两性差别来分析电影当然是浅薄的。一个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:市场上涌现出大量女性题材影片,是因为女性地位有了根本提高吗?千年社会烙印下,经过许多年的改造,甚至搬出“妇女能抵半边天”这样的标语,才好不容易才把“重男轻女”的观念从社会影响中慢慢剥离。现在,中国女性不用冠夫姓、拥有继承权、男女基本同工同酬、有生育假……这些都是进步。与我们的祖辈、父辈比起来,八零后的中国女性是相当幸福的一代人了。但我们依然面对一些实际问题,如孕期工作、家暴、代孕等,这些不是电影可以解决的。
如前所述,女性话语权的提升有助于女性主义电影市场的繁荣,但这改变不了资本市场的根本逻辑。换句话说,这类文艺作品的“泛滥”,更多是资本的选择。然而,当大家一哄而上,试图在女性题材上薅一根“羊毛”的时候,有些“知其然”也“知其所以然”的聪明人已经开始寻找下一个“流量点”了。
作为一名女性电影人,我期望看到的是,在这波女性主义电影的风潮中,有更多新生代女性导演能成长起来,用时代女性的力量来塑造女性形象、表达女性思想,为“她力量”提供更多真实的写照。无论未来市场风向如何,诚心祝愿:“好风凭借力,送[她(们)]上青云。”
彩蛋
当我遇到一部自愿免费“搬砖”的女性电影
我有一部新戏今年四月在南通开机。一样是女性主题,剧本好到我甘愿免费参与工作。故事讲述的是,一个家庭中的父亲突然离世,家中四位女性的生活因此发生巨大改变。但“改变”一定是变得更好吗?还是说,所谓“改变”,其实只是打了个转,不过换种方式重走老路呢?
这个故事最动人的地方在于:没有结局,也没有人大团圆。每个人都是继续负重前行,改变的只有身上的包袱。

电影还在拍摄中,我与观众一起期待这个全新的故事。【全】
(作者为电影人、选角导演)
图文编辑:务虚实录
欢迎扫码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务虚实录”


